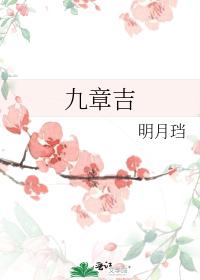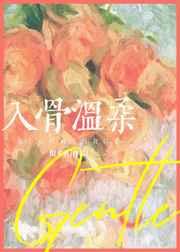自从八岁那年被哈奶奶拿剪子吓一次,又因为记住了哈奶奶话,我就再没有到老槐树根子撒尿。后来才知道,那天哈奶奶家里来的小姑娘不是客人,是她干孙女;从南边一处很远的乡下来,来了就没走。再后来就知道,小姑娘的名字叫“刘小苇”。
刘小苇是来读书的。没过几天,她就背一只新缝的两面都绣了红花的蓝布书包,到我所在的学校上学了。
她比我大一岁。我读二年级,她读一年级。
东头老街有我好几个同班同学,我们很快就认识她了。但我们不喊她“刘小苇”,喊她小名。
她小名叫“小苇子”。
“小苇子!”
“哎——”
“等我们一块走!”
“哎——”
…………
小苇子走在放学的路上,听见有人喊,就回过头,脆脆地答一声。但我们再和她说话时,她就不停用手绞着两根细溜溜的辫子,低着头,或者眼睛望着别处,不吭声。
有一次放学回来,才走进老街,我问她:
“你自己家住哪里?你爹妈怎么不来看你?”
她先不吭声,再问,嘴一瓢,竟呜呜地哭了。
因此我们很少知道她的情况,只记得她长得极瘦、极单薄,像白河滩的苇秆子;天热时穿的衣衫像挂在身上,瘪瘪荡荡的。只是她眉毛生得很好看,细细弯弯,如两道初月的牙儿。
小苇子读到四年级,快读完时,文化大革命开始,学校停课闹革命。几个月后,她又回到南边乡下。
小苇子走的那天,我带几个同学送她。
我们走在白河埂上。
那是秋天。河滩上的芦苇正开着花,秋风里芦茎摇曳,芦花翻飞,像翻动一片灰白色波浪。几只苇莺在芦丛里打闹,发出一串串清亮的啼鸣。那刻,我忽然想送她一样东西,就摘片苇叶,卷成一支芦笛,吹响了,递给她。她很高兴,说声“谢谢”。只有那一次,她把芦笛捏手里,说了不少话;说南边乡下也有很多芦苇,但没有人吹芦笛;说她家屋子是石头砌的,很厚很厚,像一座碉堡;又说她家养了几只山羊,老山羊带着小山羊,她小时候放羊就骑在老山羊背上,拿着鞭子,像骑马一样神气……
她每走几步远,就回过头和我们招一下手,依依不舍的。那刻,我分明看见她眼睛里闪烁着晶亮的泪花。
***
记得小苇子走的时候,全国红卫兵开始了大串连、先是各地学生串到北京,然后是北京学生串到各地,再然后就乱串。白河镇红卫兵也参加串连。他们当中多数人是跟着棠川县城红卫兵一起出去的,出去一批,回来一批;回来一批,又出去一批。直到过年的时候,也就是一九六七年春节,才一个个蓬头垢面,黑干憔悴,又有冻得青头紫脸的,回到家。可惜没有全部回来。因为其中一队红卫兵要学习老红军,重走革命路,在井冈山至南昌一带徒步一个多月,途中累死一名女生——一说病死,失踪一名男生。
那时候我在白河镇中心小学读六年级。那年冬天特别冷,一场大雪后,家家檐口挂了二三尺长的冰锥。有小朋友推着小板凳在白河上面滑冰。河滩上偶见没有割掉的苇秆,像晶亮的银条在寒风中抖动。因为天太冷,外公不让我出门,教我练毛笔字。我就趴在南边窗口一张能照到阳光的小桌子上,临欧阳询的《九成宫》。
外公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小文人,爱棋琴,擅书画,说话慢条斯理。他祖上几代行医,自己年少时却梦想入仕。但时至清末,他十七岁考秀才过了县试府试,剩院试一关;未料当年清廷下旨,废了科举。后来他做过几年儒学训导,以后就一直在白河镇教书。
外公平时很关心时事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阵子,他显得烦躁,坐不住,经常喃喃地念叨:
更多内容加载中...请稍候...
本站只支持手机浏览器访问,若您看到此段落,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,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、畅读模式、小说模式,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,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!
本章未完,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!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,请尝试点击右上角↗️或右下角↘️的菜单,退出阅读模式即可,谢谢!